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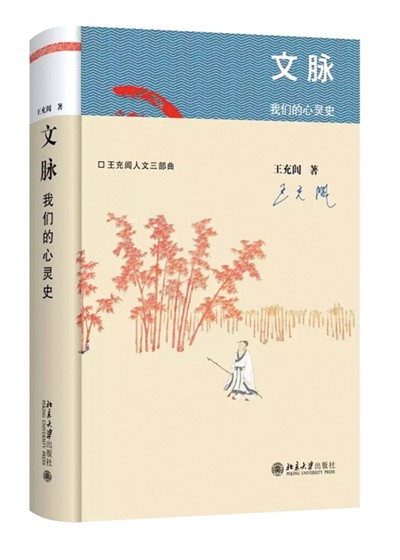

王充闾 郭红松绘
与曾国藩相比,我更钦佩张謇。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曾国藩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居京十载,他中进士,授翰林,遍任各部侍郎。外放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位列三公,成为清代立国以来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达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内圣外王,“不愧天地之完人”。
然而我却隐隐觉得他丧失了本我和生命的出发点。他既要建非凡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实现内外的全面超越,他的痛苦也同样来自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对他的忌惮猜疑,同时为树立完美形象,言行谨慎,如履薄冰,事事追求圆满,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
与之相比,张謇犹如长夜先行者。
张謇的科举路很不平顺。眼见甲午战败,思及26载蹉跎、120个昼夜在窄小考棚白天答卷晚上蜷缩休息的经历及八股文对人才的摧残,状元及第的他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确立“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后,他先后创办20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桑蚕、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行业。他兴办的370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以及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职业教育。他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酝酿将高师改大学,东南大学由此成立,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他摸索出的“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教育文化方面,他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新式剧院以及气象台等,均在全国首开先河。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公园、体育场的同时,他还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疾院、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慈善事业,着眼于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在思想理论建树方面,学术界一向有“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评价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好比在固有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更着眼于创新,致力于重起楼台。张謇作为开创型实践家,当属后一类。从历史学角度看,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黎民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愚于近人,颇服张謇。”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张謇,乃至中国历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们在所处时代中的所述、所为,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影响,并以自己的实践丰富着这一文化。这也是我写《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所选取的角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血脉与命脉,国学是中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拥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为中华民族增添了高度的自信和无比的自豪。
不少人将国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这是不科学、不严谨的,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有物质文化(如器物、服饰、饮食、建筑等)、制度仪式文化、精神文化(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而国学,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范畴相对狭窄。
所谓“国学”,是相对于西学、新学而言的。清代末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称为“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梁启超说,国学是关于道德品性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学问。以学科分,国学包括今天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诸子百家、儒道释三家学说等。长期以来,儒学贯穿并主导着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于从属地位。
从学理上讲,中华传统文化有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传入、传播,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中华传统人生智慧,相生相发,相辅相成。儒家讲求入世进取,强调刚健有为,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究精神超脱,道法自然,安时处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佛家讲究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干扰,化烦恼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为上”。从前有个说法:“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语)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有些历史文化散文,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心灵的枯竭、弥补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性,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主体,见不到心灵展示的维度。我在写作中,特别注意强化主体意识,注重现实的针对性,努力把新见解、新发现、真性情、现实感灌注到史料之中。
历史文化散文应该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是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它们应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用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
写作《文脉》一书时,我在准确理解古籍的前提下,采用散文形式、文学手法,交代事实原委,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尽量设置一些张力场、信息源、冲击波,使其间不时跃动着鲜活的形象、生动的趣事、引人遐思的叩问,努力避免纯政论式的沉滞与呆板,说理则成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醒或是对抒情、叙事的必要调剂。这种“理”,来自对生活的感悟,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这样,历史也变得灵动起来,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
中华文脉浩浩汤汤。我们走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走向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走进汹涌澎湃的心灵世界。(王充闾)
,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