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履生:我的画画之路
来源: 陈履生美术馆

陈履生画丈二迎春《律向韶阳变》
画画并不是我的理想。如果说儿时的涂鸦与未来走向职业艺术生涯有必然联系的话,那么,普天下应该都是艺术家。每位画家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经历,但早期的相似性可能在属于同一时代的画家中都有着基本的框架。1978年的夏天,当我从县教育局拿到南京艺术学院的入学通知书回到家之后,家里好像并没有什么激动,非常平静,我自己也是如此。因此,几十年之后都在想为什么没有欣喜若狂的状态,更不解那个范进中举为何疯癫。根本的问题是当时还没有预料到这是改变人生的关键一步。爷爷倒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家本来就是读书的”。
我曾经的第一理想是当兵。因为像我这样的家庭中如果能够出一个军人,不仅是“全家光荣”,更重要的是将会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每到新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就会敲锣打鼓送来“光荣家属”的春联,那真是无上的荣光。毫无疑问,一身军绿是那个时代中无数青年的理想和时尚。按理说有家中兄弟四人这样丰厚的人力资源最有可能报效祖国的国防,可是,仗打不起来,“苏修”也只是不断叫嚣而已,所以,枉费了青春时代的梦想。然而,枉费的代价不仅是梦想的落空,更重要的是抽掉了通向光明前途的唯一的跳板,还必须面对现实中的政治压力。无形的政治紧箍咒一直紧紧地套在头上,真不知道如何能够解脱。因此,有了写字画画那另外一条途径。当年,在家乡的这条路上形单影只。在别人看来,那是一门手艺,大家所认同的是需要天分和爱好,所以,不争不抢。不像当兵那样争先恐后。
一切好像都不是想象的那样。真的不是为了艺术,也确实不知道艺术为何物。就知道字要写得端正,写柳公权要像柳公权,画张三要像张三,完全是民间艺人的感觉。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缺少基本的艺术启蒙。实质性的变化是考上大学之后,正规的训练,从素描到色彩,从头像到人体,从静物到风景,从工笔到写意,从二方连续到四方连续,从印染到织绣,从写生到创作,从文学到史论,从中国到外国,一环套一环,转眼过去了四年。此后为了改变图案专业这一好像是低人一等的出身,改学了美术史论中的中国美术史,又是三年,得了一个在今天好像都不值得一提的硕士学位,却慢慢地远离了绘画,一时间画笔都不知道去哪里了,也没有去想将来成为画家,从道路上看是离绘画越来越远。可是,对于艺术的认识却日益提高,钻到书堆里也是不亦乐乎,而码字从手写到敲键盘,文字量不断累积,逐渐成了评论家或理论家,并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社会形象。由此,想写的和不想写的与日俱增,难以停息,写写也烦了。关键是画画的心不死,还是想画画。这时画画成了理想。
重拾画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真心不忍舍弃之外,就是实在不满画坛的现状,应该重操旧业,加入到千军万马的绘画队伍之中,以考验自己这么多年理论研究的成果,也是验证当年的基础和当下的努力。另一方面的理论依据是,在20世纪的著名画家中,傅抱石在中央大学是教美术史的,潘天寿写过《中国绘画史》,黄宾虹还编过《美术丛书》,从史论家到画家,从画家到史论家,之间好像没有任何障碍,相反,彼此的融通,更加能够促进两方面的发展。这好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确实,史论与绘画关系紧密,尤其是文人画,无文则无画。因此,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主楼外东南角的画廊办了平生第一次个展,很多师长或朋友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心里在说“你还会画画”?就这样直到今天,圈内的人也没有将我看成画家,也没有认认真真看过我的画,好像还是不屑一顾。这都无所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感觉,以及对当代中国画现状的看法,对当代中国画未来走向的判断。
2015年的9月13日在广州办了绘画、书法、摄影的系列展,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个展览是提出了问题,即“务本”的当代意义,个中许多问题需要时间去论证,因此,在轰轰烈烈回归平淡之后,需要思考中国水墨与文人传统,更需要实践去探索没有尽头的书法与绘画。
学画迄今四十载,专业工作三十年,在毫无感觉的时光流逝中,不知不觉已然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接着是什么……是艺术的召唤而开启新的航程和新的路向。
(此文为《陈履生画集》前言,2016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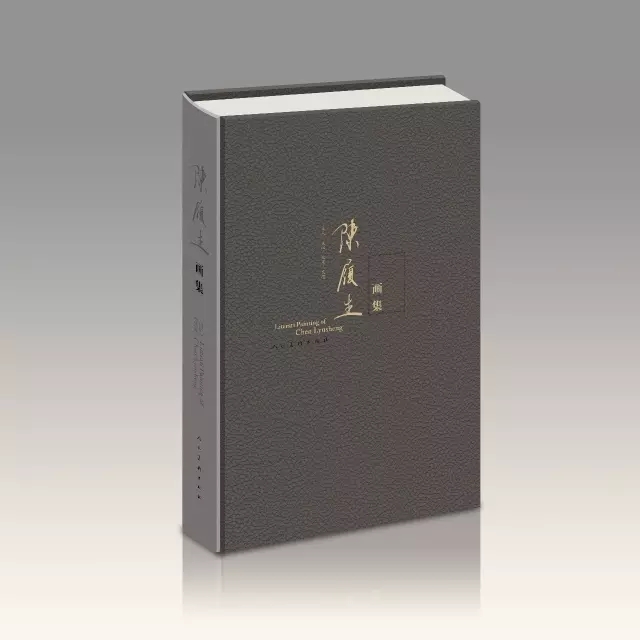

陈履生1977年上大学前的水墨速写《外婆》
 友情链接
友情链接